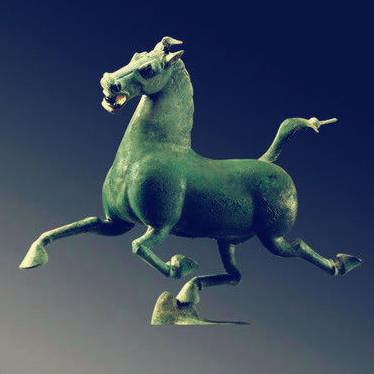(来源: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浅析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上)
纵使中非远隔万里,也并没有阻挡两地人民互通有无。中国与非洲的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当时中非的交流的货品还是以丝绸、象牙和犀角为主,而中国瓷器与非洲的第一次相遇已然是在晚唐五代时期,且这种贸易的形式一直持续到清代早期。
中国的瓷器怎么来到了非洲?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路线,元代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的《游记》中就记录了一条完整的从泉州销往印度,然后再转卖到阿拉伯半岛、北非地区的瓷器贸易路线,可以看出中国——东南亚——印度、中东地区——非洲地区是对这条海上路线的整体概括。相对于丝绸,瓷器的到来似乎晚了一些,但是对非洲造成的影响却是空前的,非洲地区的经济、技术和社会都受到来自中国瓷器的深远影响。
01
北非的瓷器集散地
北非最早进行瓷器贸易的是中世纪埃及的福斯塔特(Fostat,今开罗旧城),也是持续时间最长,出土瓷器数量最多的遗址。在公元7世纪中期,伊斯兰力量从拜占庭帝国手里夺去了埃及,但因为当时的政治中心——亚特兰大普遍奉行基督教,阿拉伯人决定在驻军的地方——福斯塔特(名字意为“帐幕”,军营的意思)建立政治中心,在不断地建设和扩张中,也使得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福斯塔特城,经济活动十分繁荣。福斯塔特的繁荣一直延续到了12世纪中期,法蒂玛王朝为了阻挡狂热的欧洲基督徒们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决定实施焦土政策,把福斯塔特城付之一炬。然而,福斯塔特并没有就此倒下,很快随着法蒂玛王朝的垮台,阿尤布王朝和马木鲁克王朝当政,福斯塔特又成为了贸易的中心,瓷器贸易还在繁荣地进行着。虽然经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福斯塔特还是在1347-1349年的黑死病瘟疫狂潮中倒下了,加上尼罗河的改道,福斯塔特失去了港口的地位,从此一蹶不振,逐渐成为新建的开罗城的垃圾倾倒地。
(图一)埃及福斯塔特遗址
直到20世纪初期,埃及政府开始发掘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尘封的面目终于再一次呈现在人们眼前。在这个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来自中国的瓷器,年代持续时间在公元9世纪到公元18世纪初,即从中国晚唐五代时期一直持续到清代早期,也就是说中国持续往福斯塔特地区输送瓷器,并持续了近千年,这见证了历史悠久的中非商贸史。
古代埃及的福斯塔特是非洲地区最为著名的陶器生存基地,具有悠久的生产历史,同时也是当时的埃及经济贸易中心,商业贸易繁荣,加上阿拉伯人的擅长贸易经商,大量来自外国的商品被运到这里进行售卖,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瓷器。或许正因为有着丰富的使用陶器的历史,当中国的瓷器一出现在埃及,就在社会上层人群中流行起来。
在福斯塔特流行的中国瓷器种类繁多,不同时期流行的窑口和样式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及外销情况,具体参见表一。
年代 |
类型 |
瓷片数量(片) |
唐至五代时期 |
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青釉铁绘器和巩义窑白釉绿彩陶器。 |
约40 |
北宋时期 |
越窑青瓷、西村窑、景德镇青白瓷、定窑、磁州窑和耀州窑。 |
约1300 |
南宋时期 |
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 |
数十件 |
元代时期 |
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 |
约4350 |
明代时期 |
景德镇、漳州窑和德化窑。 |
约1200 |
清代早期 |
青花瓷、五彩瓷、粉彩瓷和单色釉瓷 |
约5400 |
(表一)福斯塔特出土中国瓷器情况
由于埃及社会对于中国瓷器需求巨大,却因为供应十分有限而且十分珍贵,只能为社会上层人士所使用,中下层居民难以获得。为了满足中下层居民的需求,所以当时的一些埃及的能工巧匠开始利用本土的制陶技术来对中国瓷器进行仿制,并且生产了大量的颇有地方特色的“仿中国陶器”,这些陶器在釉色、形制、纹饰、风格都很接近中国瓷器,而且这些陶器出土占比达到70-80%,可见埃及人对中国瓷器的喜爱。
中国的瓷器在不断的贸易交流中逐渐扩散到了埃及的其他地区,包括埃及的亚历山大、库赛尔、阿斯旺和努比亚等地。北非其他地区也发现了中国陶瓷的身影,苏丹的埃得哈布港和摩洛哥,这些著名的沿海港口也有中国瓷器的身影。
参考文献:
- 马金鹏 . 伊本 · 白图泰游记 [M].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
- 三上次男, 李锡经, 高喜美 . 陶瓷之路 [M]. 文物出版社, 1984.
-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 [M]. 紫禁城出版社, 1987.
- 沐涛主编;许永璋著 . 古代中非关系史稿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
- 夏鼐 . 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 [J]. 文物, 1963(01).
- 秦大树 .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 [J]. 海交史研究, 1995(01):79-91.
- 丁雨 . 肯尼亚滨海省马林迪老城遗址的初步研究 [J]. 南方文物, 2014(04):130-138.
- 丁雨 . 中国瓷器与东非柱墓 [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7(05):133-145.
- 陶泓铮 . 瓷器视角下唐代以来的中非交流 [J]. 今古文创, 2021(14):49-50.
- 申浚 . 非洲地区发现的元明龙泉窑瓷器 [J]. 考古与文物, 2016(06):110-117.
- 秦大树 . 肯尼亚格迪古城和蒙巴萨沉船出土明清瓷器及相关问题讨论 [J]. 考古学研究, 2019(00):405-521.
- 秦大树 . 在肯尼亚出土瓷器中解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 [J]. 中国中小企业, 2018(10):61-65.
- 弓场纪知,黄珊 . 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 1998-2001 年研究成果介绍 [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6(01):120-163.
- 叶书涵 . 贸易及其他因素对开罗城市发展的影响探究 [J]. 建筑与文化, 2021(09):61-63.
- 田明,苏玉雪 . 古埃及与阿克苏姆的文明交往 [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7(01):44-50.
- 秦大树 . 在肯尼亚出土瓷器中解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 [J]. 中国中小企业, 2018(10):61-65.
- 铃木重治,任汶 . 肯尼亚 · 坦桑尼亚出土的中国陶瓷——从 1987 年的实地考察谈起 [J]. 南方文物, 1992(04):121-126.
- 工凡 . 坦桑尼亚出土的中国陶瓷器 [J]. 中国科技史料, 1993(01):49.
- 丁雨 . 东非沿海地区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器 [J]. 考古, 2017(09):109-120.
- 伊夫 · 波特,翟毅 . 十四至十七世纪伊斯兰宫廷的龙泉青瓷器 [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09):78-93.
- Chapurukha M. Kusimba, Tiequan Zhu, Purity Wakabari Kiura. China and East Africa Ancient Ties and Contemporary flows: A Critical Appraisal[M].2020.
- Montella A. Chinese Porcelain as a Symbol of Power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from the 14th Century Onward: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unerary Context[J]. Ming Qing Yanjiu, 2016, 20(1): 74-93.
- Zhao B. Chinese-style ceramics in East Africa from the 9th to 16th century: A case of changing value and symbols in the multi-partner global trade[J]. Afriques. Débats, méthodes et terrains d'histoire, 2015 (06).
- Zhao B . Global Trade and Swahili Cosmopolitan Material Culture: Chinese-Style Ceramic Shards from Sanje ya Kati and Songo Mnara (Kilwa, Tanzania)[J].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12, 23(1):41-85.
图片来源:
图一:[日]弓场纪知——《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1998-2001年研究成果介绍》
数据来源:
表一:[日]弓场纪知——《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1998-2001年研究成果介绍》
来源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供稿 | 黄琳梓
编辑 | 冯东伟
本微信公众号法律顾问: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卢锐湘律师
▼欢迎转载,转载前请联系我们▼
▼广东海丝馆 网上商场
责任编辑: